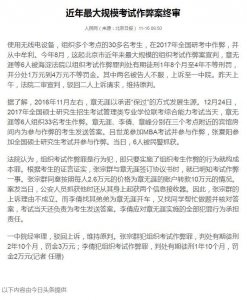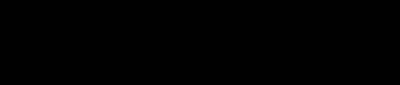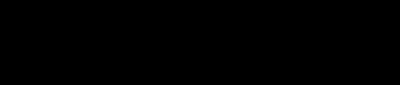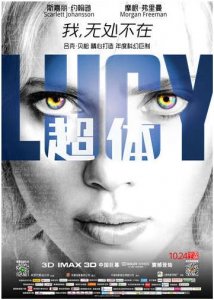《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》火爆的背后,是台湾悲情电影的一脉相承

文 / 观影君
3月份大片扎堆,在此之前,或许没有人想到,能杀出重围创造票房奇迹的,竟会是这部来自台湾的翻拍电影—《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》。

《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》海报
即使是在3月22日,五部新片同时上映“围剿”的情况下,也没能动摇它票房第一的宝座。除3月14日上映首日外,《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》已经势如破足地连续12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。
当前累计票房已突破8.3亿,成为内地最卖座的台湾电影,并将第二的《我的少女时代》(3.58亿)远远甩开,有望冲击10亿大关。
《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》翻拍自2007年的韩国同名电影,上映前就在抖音玩起了“悲情营销”,就连海报上也赫然写着“唯一观影提示:请带足纸巾”。

唯一观影提示:请带足纸巾
有别于近些年来台湾电影的温情底色,《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》再一次回到了台湾电影最初的本源,那就是“悲情”二字。
1、 台湾悲情片的起源
谈及上个世纪的台湾电影,常常与“悲情”挂钩。1989年,侯孝贤导演的《悲情城市》为华语电影首次赢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,标志着台湾悲情电影的鼎盛时期。

侯孝贤《悲情城市》(1989)
“悲情”不仅仅代表着20世纪80至90年代期间台湾电影的叙事风格,更是50年代至60年代末台湾电影的本源台湾民众们的文化诉求。
1949年,由厦门移民至香港的戏曲人员以闽南语为对白,拍摄了一系列电影,被称作“厦语片”。
当时的台湾,会讲闽南语的台湾客家人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四,这些“厦语片”流入台湾后,赢得了他们极大的喜爱,因为能在大银幕上听见乡音。甚至后来这些“厦语片”直接被冠以“正宗台语片”的称号。

“厦语片”剧照

“厦语片”剧照
为夺回“正宗台语片”的称号,台湾本土的电影人开始效仿“厦语片”的拍摄套路,以台湾的歌仔戏为故事雏形,汲取闽南方言文化提供的民间文化创意,也拍摄了一系列台语片。
在1955年,叶福盛导演拍出了最早的台语电影《六才子西厢记》。紧接着在1956年,何基明导演也拍摄了台语电影《薛平贵与王宝钏》。
在争夺“正宗台语片”称号的拉锯战中,五十年代末的台湾电影几乎都是台语片。但无论是厦语片的“哭调子”还是歌仔戏的苦情剧,这些电影都离不开悲情的创作本源和叙事策略。“悲情”成了台语片一个鲜明的标志,也是台湾电影的底色。

侯孝贤《悲情城市》(1989)
到了电影制作技术更为成熟的60年代,台语片在创意上还是跳不出歌仔戏的悲情戏码,比如梁哲夫导演的《高雄发的尾班车》和《台北发的早车》,还有邵罗辉导演的《旧情绵绵》,都讲述着台湾底层小人物生活的悲苦和艰难。

梁哲夫《高雄发的尾班车》海报(1963)

梁哲夫《台北发的早车》海报(1964)
与此同时,台语片所尽力渲染的悲情也影响了台湾国语片的情感表达,代表作当属李行导演的《街头巷尾》,《蚵女》以及《养鸭人家》。
影片中的悲情被处理得更为细腻,时隐时现,相较于台语片的悲情而言,国语片中的悲情多了几分现实意味,由歌仔戏的戏剧社会升华至了现实社会。

李行《蚵女》公映海报(1972)
1955到1969年的这十五年间,台湾共拍摄了1425部电影,其中台语片1052 部,国语片只有373 部。其中台语片在没有赞助和投资的情况下,其资金全部来源于民间,因此,电影中的悲情也可被视为一种迎合大众的文化产品,能引发台湾民众们深深的共鸣。
2、 台湾悲情片的转型与延续
进入20世纪70年代,台语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。究其原因,一方面是许多知名导演开始将重心转向国语片,台语片面临着人才流失、粗制滥造、创意枯竭等问题;
另一方面,台湾当地开始推广国语教学,新一代的台湾观众对乡音不再过度敏感,对台语片的认同也逐渐淡化。
虽然台语片走向没落,但是以悲情为基底的情感结构却并未随之消失,反倒是在之后的台湾“新电影”运动中保留了下来。并且旧时台语片中对台语的使用、对乡村的眷恋、对台湾本土文化的认同,也一并保留了下来。
1982年,四段式的电影《光阴的故事》拉开了台湾“新电影”运动的序幕。一直到90年代,台湾“新电影”运动将这种悲情的延续推向了最高潮,这其中的弄潮儿自然就是侯孝贤和杨德昌导演。

杨德昌《光阴的故事》(1982)
侯孝贤导演的《童年往事》、《悲情城市》、《戏梦人生》、《好男好女》等多部悲情影像作品,着眼于个体,以及由个体组成的家庭,通过个体与家庭的浮沉聚散来反映台湾社会的历史变迁,群体追思与国家记忆并行,创作了了独具特色的“悲情系列”。

侯孝贤《童年往事》(1985)
杨德昌导演则将悲情叙事融汇到了台北都市之中,没有大起大落的悲情宣泄,反倒更多地诉说着都市生活中的身不由己和无可奈何。那种悲情,是温水煮青蛙式的。
杨德昌说过:“台在台北,许多生活的问题都已逼到门口来了。我的电影是做客观的观察,台北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,我也没有办法替他们解决。但我的电影可以有提醒的作用。有人说《恐怖分子》的结局非常绝望,但我认为,电影的结局虽然绝望,却因此让我们必须思索避免绝望的结局。”

杨德昌《恐怖分子》(1986)
在“新电影”运动中,悲情仍是“主角”,只是换了一种出场方式罢了。悲情被藏得更深,表露得更少,但是带来的感官刺激却丝毫不减当年。在侯孝贤和杨德昌极度 “作者化”的操作下,悲情成了一种欲言又止的现代派实验。
这种私人化的任性表达,仰赖于台湾新闻局“电影辅导金”的资金辅助,鼓励导演进行创作,而不用过多考虑票房的压力。台湾电影在海外拿奖无数,知名度也大幅提升。

侯孝贤《好男好女》(1995)
可是此等做法也使得台湾电影与本土产业严重脱节,华语电影占据台湾放映市场的份额也从1992年的50%跌落至2000年的2%,而好莱坞电影却从1992 年不到50% 的市场份额一路飙升到2000年的98%。
伴随着“新电影”和“新新电影”运动的发展,悲情,已经无法再充当台湾电影的保护伞了,它正成为一种背对观众们的艺术行为。
3、温情对悲情的僭越
进入新世纪,在全球化语境中,台湾电影渴望本土化的繁荣。于是,台湾新世代导演开始寻求台湾电影“从悲情到温情”的过渡,决心重建台湾电影新的文化创意产业结构。他们淡化和削弱了台湾电影一以贯之的悲情色彩,践行着由悲情向温情的不断过渡。

魏德圣导演
2008年魏德圣导演的《海角七号》是一部里程碑式的电影,它为死气沉沉的台湾电影市场注入一针强心剂,拿下了5亿新台币的高票房。
《海角七号》改变了早期台语片和新电影运动以来台湾电影的悲情和残酷,通过温情脉脉地诉说台湾本土的故事,回顾和反思台湾的历史和过去,吸引了无数本土观众重新走进电影院观看台湾电影,拒绝好莱坞的垄断,也宣告了台湾电影从“悲情乡土”到“温情本土”转变的开始。

魏德圣《海角七号》(2008)
2009 年何蔚庭导演的《台北星期天》,讲述了两个在台北工作的菲律宾工人,搬着从路边“捡来”的沙发横穿台北的故事。片尾以超现实的表现手法表现两人坐在沙发上仰望星空的想象。虽是底层故事,却毫无悲伤之感。

何蔚庭《台北星期天》(2010)
2010年陈骏霖导演的《一页台北》同样大获成功,电影讲述了男主角放弃了远赴法国找寻前女友,而是留在本地开始一段新恋情的温情故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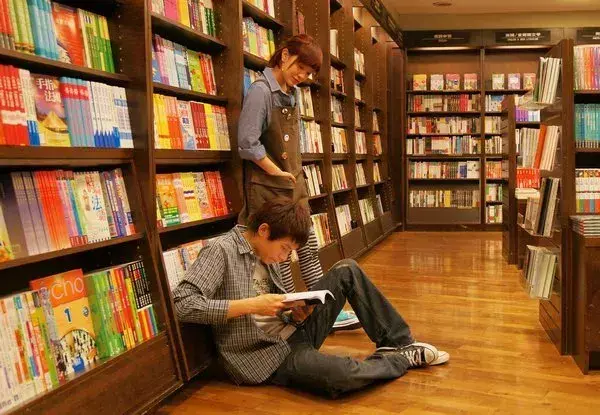
陈骏霖《一页台北》(2010)
从2008年的《海角七号》以来,“从悲情到温情”的转变进行得很成功,从《台北星期天》、《听说》、《不能没有你》再到《那些年,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》等电影,温情作为主旋律,不仅只是台湾新世代的影像风格,甚至可能调和或淡化社会文化冲突。

九把刀《那些年,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》(2011)
台湾本土电影市场也肯定了这一转变,观众纷纷为其买单,对复苏、繁荣台湾本土电影市场具有积极的意义。
4、结语
回顾台湾电影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今的七十年发展历史,可以说台湾电影的根源就是“悲情”。
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,台湾电影经历了从“悲情”过渡到“温情”十年。《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》在这个时间点,选择以台湾电影最初的样子杀进内地市场,击中了无数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。

林孝谦《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》(2018)
“从悲情到温情再到悲情”,生活压力的增大,情绪上的共鸣开始被重视。悲情或是温情,都会被无限放大,形成一种社会效应。
很多人的生活是满的,没有情感宣泄的出口,难得走进电影院,还要面对好莱坞动作大片的轰炸,更是难以喘气。

林孝谦《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》(2018)
《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》的到来,你可以说它不合时宜,但对有些人来说,就是恰逢其时。一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台湾观众乐于观看悲情电影一样,七十年后,内地的观众同样也盼望着一部这样的电影。
(完)